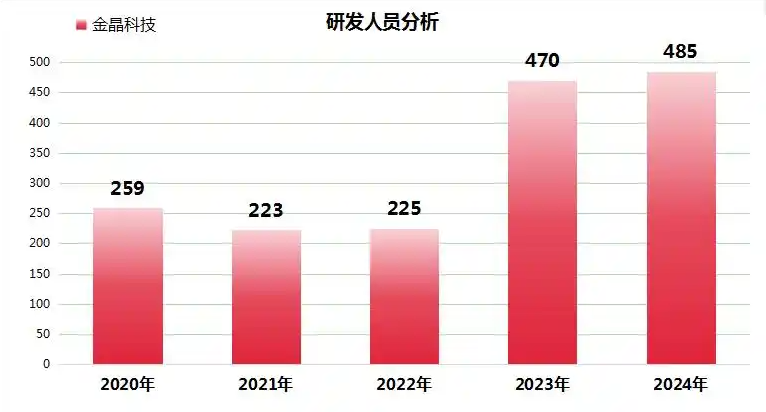日前,值“四海通達(dá)——海上絲綢之路(中國段)文物聯(lián)展”在廣州舉辦之際,著名考古學(xué)家、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及原漢唐研究室主任、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研究生院考古系博士生導(dǎo)師、德意志考古研究院通訊院士安家瑤,在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接受了新快報收藏周刊記者的專訪。作為國內(nèi)外最早開展中國古代玻璃研究的學(xué)者,她以與其淵源頗深的南漢康陵出土玻璃瓶為切入點(diǎn),為我們講述了一段“玲瓏透澈、繽紛東西”的“絲路”玻璃故事。
安家瑤
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原漢唐研究室主任,原西安研究室主任;中國社會科學(xué)院研究生院考古系博士生導(dǎo)師;西北大學(xué)兼職教授;德意志考古研究院通訊院士。長期從事唐長安城的考古發(fā)掘和研究,主持多項重要考古發(fā)掘。在中國古代玻璃器研究方面有深入研究。
與廣州、與康陵玻璃瓶的緣分
收藏周刊:安老師,您好。日前,作為專家代表,你出席了正在南越王博物院舉辦的“四海通達(dá)——海上絲綢之路(中國段)文物聯(lián)展”開幕式,今天,您又來到了南漢二陵博物館觀展。
安家瑤:是啊,這是我頭一次來參觀這座年輕而豐富的展館。不過,我與這座博物館、與廣州的不解之緣,數(shù)十年前已深深結(jié)下。南越國宮署發(fā)掘之時,我有幸成為合作的第一任隊長;2003年康陵發(fā)掘之始,我亦受麥英豪先生邀請而來,其時大家還在研究此處是否為南漢祭天圜丘。后來確認(rèn)是南漢開國皇帝劉巖的陵墓——康陵,還有哀冊文碑,我非常高興,而且這里還出土了玻璃殘片。
收藏周刊:藏于南漢二陵博物館、目前正在“四海通達(dá)”展出的一件綠色玻璃瓶,是您當(dāng)年親自研究過的嗎?
安家瑤:對。這件玻璃瓶是康陵出土的上百件玻璃碎片中能夠修復(fù)起來的唯一一件,尤其珍貴。
收藏周刊:作為國內(nèi)外最早開展中國古代玻璃研究的學(xué)者之一,您如何看待這個玻璃瓶,在玻璃研究史乃至海上絲綢之路遺產(chǎn)研究范疇里的地位和意義?
安家瑤:玻璃,我們要看時代和其在時代中的地位。在已知的考古發(fā)掘和博物館收藏中,還沒有見到與(這件康陵玻璃瓶)完全一樣的玻璃器,但在伊斯蘭玻璃中卻有相似的器形和相同的裝飾。康陵出土玻璃殘片可以看出器型的直口鼓腹玻璃瓶和侈口長頸鼓腹玻璃瓶也是伊斯蘭玻璃器的常見器形。分析這批玻璃殘片的制作工藝和化學(xué)成分,可以得出康陵玻璃是伊斯蘭玻璃的結(jié)論。
南漢康陵出土的伊斯蘭玻璃是對歷史文獻(xiàn)很好的印證。廣州自先秦時代便是海上交通的重要港口。自漢至唐,廣州在中國海上交通和貿(mào)易的地位越來越重要。唐代宗視琉璃盤為珍寶的故事也發(fā)生在廣州——
代宗大歷八年(773年),路嗣恭前往廣州平叛哥舒晃叛亂,平定后,獻(xiàn)給唐代宗一個玻璃盤,直徑九寸,代宗以為“天下至寶”。不久,宰相元載獲罪被抄家,一個直徑達(dá)一尺的玻璃盤被抄出,這個玻璃盤也是路嗣恭平定嶺南后送給元載的。代宗發(fā)現(xiàn)路嗣恭竟然沒把最大的玻璃盤貢獻(xiàn)給自己,心中非常不快。路嗣恭在廣州得到的玻璃盤,應(yīng)是從阿拉伯帝國運(yùn)來的西方玻璃,正因這種玻璃盤在中國很難得到,所以代宗“以為至寶”。
從考古出土的玻璃器可以看出,中國古玻璃一直存在著兩個系統(tǒng):進(jìn)口玻璃和國產(chǎn)玻璃。這兩個系統(tǒng)不僅存在于隋唐之前,也存在于隋唐之后。通過陸路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從西方進(jìn)口的玻璃器,一直是中國上層社會競相追逐的時尚奢侈品。中國國產(chǎn)玻璃的產(chǎn)生和發(fā)展,與東西文明的交流和碰撞相關(guān)聯(lián)。雖然玻璃在古代沒有發(fā)展為中國主要的手工業(yè),但是中國玻璃具有很強(qiáng)的傳統(tǒng)文化印記,清新獨(dú)特。
自戰(zhàn)國到北宋一直存在兩類系統(tǒng):進(jìn)口玻璃和國產(chǎn)玻璃
收藏周刊:目前我國發(fā)現(xiàn)最早的玻璃珠子,是否就在春秋末戰(zhàn)國初?
安家瑤:對。最早它們是進(jìn)口的,但,您知道中國人模仿能力特強(qiáng),很快我們就可以用自己的材料,制造出外觀相似,甚至更漂亮更大的珠子。
收藏周刊:這個“超越期”是幾時?
安家瑤:戰(zhàn)國。戰(zhàn)國早期墓里,出土有進(jìn)口“蜻蜓眼”,中期則大量出現(xiàn)國產(chǎn)品。譬如戰(zhàn)國中山國王厝的陵,其出土“蜻蜓眼”質(zhì)地就有鈉鈣玻璃和鉛鋇玻璃,也就是既有“進(jìn)口”又有“國產(chǎn)”。
收藏周刊:珠子是否是最早的玻璃器?如何從成分上分辨進(jìn)口玻璃和國產(chǎn)玻璃?
安家瑤:據(jù)考古發(fā)現(xiàn),世界最早的玻璃誕生在公元前2500-2300年的美索不達(dá)米亞,即今天伊拉克地區(qū)。玻璃誕生后經(jīng)上千年磨煉,才從制作小件玻璃飾品,發(fā)展到制作玻璃容器。
關(guān)于中國玻璃的起源學(xué)界尚無定論,但從考古出土玻璃器可看出,自戰(zhàn)國到北宋,我國一直存在兩類不同系統(tǒng)的玻璃制品:進(jìn)口玻璃和國產(chǎn)玻璃。西亞玻璃多用蘇打做助熔劑,稱之鈉鈣玻璃。而中國在歷史上大概是缺少自然純堿資源,所以國產(chǎn)玻璃多以氧化鉛作為助熔劑,生產(chǎn)的多是鉛玻璃:戰(zhàn)國兩漢的鉛鋇玻璃、隋唐的高鉛玻璃、宋元的鉀鉛玻璃。
收藏周刊:成分為鉛鋇玻璃,是否就基本認(rèn)定是國產(chǎn)?
安家瑤:對。
收藏周刊:鉛鋇玻璃和鈉鈣玻璃有什么明顯區(qū)別?
安家瑤:早期國產(chǎn)玻璃器皿含鉛,玻璃的折射率高于鈉鈣玻璃,所以其光澤比進(jìn)口玻璃要好。鉛玻璃本身缺點(diǎn)是化學(xué)穩(wěn)定性差,不耐腐蝕,所以出土的玻璃器皿大多已失去當(dāng)年美麗,暗淡無光,并常附著厚厚的黃白色風(fēng)化層。國產(chǎn)玻璃器皿在造型上的特點(diǎn)是小型器皿多、薄壁器皿多,器形基本保持了中國器物的風(fēng)格。
從前人們把“天然”玻璃當(dāng)成至寶
收藏周刊:在中國漫長的器物發(fā)展史上,玻璃制品是否曾出現(xiàn)過繁榮時期?它是怎樣和我們的民族審美傾向融合的?
安家瑤:中國玻璃的誕生可能受西亞影響,但新建起的玻璃業(yè)很快與中國文化傳統(tǒng)相融合,開始生產(chǎn)玉的仿制品。先民一直對玉追崇備至,質(zhì)地看來相近的玻璃成為玉的代用品,玻璃衣、玻璃九竅塞、玻璃琀和玻璃“握玉”等“葬玉”出現(xiàn)。玻璃璧作為玉璧的代用品,自戰(zhàn)國中期在湖南地區(qū)就廣泛用于喪葬。玻璃璧在西漢時期還繼續(xù)使用。2009-2011年江蘇盱眙大云山漢墓則出土了22件玻璃磐,其尺寸與石磬相仿。漢代就能夠制造這樣大型的玻璃器,這令我們對當(dāng)時玻璃制造業(yè)的規(guī)模和技術(shù)刮目相看。
收藏周刊:當(dāng)時我們自己制造玻璃的工藝,跟西方相同嗎?
安家瑤:我們主要還是鑄造的、模壓成型,較富于中國特色。玻璃制造一向“小眾”,社會動亂時,它可以一下子失傳。我們看漢代玻璃璧那么流行,一到戰(zhàn)亂,幾乎消失。
收藏周刊:它的重盛是在什么時候?
安家瑤:也是因絲綢之路。《魏書》本紀(jì)記載中亞人,曾到北魏都城平城(今山西大同),為中國帶來玻璃制品工藝。
魏晉南北朝時期,南方的東西交通路線繼承了兩漢的傳統(tǒng),仍然以水路為主,僅南京東晉墓就出土七件羅馬玻璃。這個時期文獻(xiàn)對海路輸入玻璃也有記載,《吳歷》記:“黃武四年,扶南諸外國來獻(xiàn)琉璃。”這個時期的北方,多依靠陸路交通。西晉詩人潘尼在《琉璃碗賦》中說:“覽方貢之彼珍,瑋茲碗之獨(dú)奇,濟(jì)流沙之絕險,越蔥嶺之峻危,其由來阻遠(yuǎn)。”明確記載了玻璃碗通過絲綢之路輸入我國,與新疆發(fā)現(xiàn)多處羅馬玻璃殘片相符。
收藏周刊:接著我們又開始仿制嗎?
安家瑤:最初他們的工匠可能也過來了。后來也是仿制,制咱們喜歡的東西。
收藏周刊:自古以來,國人似乎都對玻璃這種材質(zhì)挺感興趣的?
安家瑤:在很長一段時間,人們分不清玻璃是天然還是人工,于是把它當(dāng)成珍寶。您看顏師古,作為唐代大學(xué)者,他就認(rèn)為國內(nèi)玻璃是人工的,進(jìn)口玻璃是天然的。中國人有個觀念,覺得人工的就不值錢,天然的才珍貴。直至宋代,大家才漸漸知道玻璃乃人造。蘇軾有首詩,頭兩句是“镕鉛煮白石,作玉真自欺。琢削為酒杯,規(guī)摹定州瓷。”作玉真自欺,那時他們就知道玻璃是人工制品了。
收藏周刊:按照您的研究,大概從什么時候開始,中國在玻璃制造工藝上,開始和國外技術(shù)同軌?
安家瑤:那比較晚了。到清代,康熙很喜歡西方的玻璃,一些傳教士本身也會玻璃技藝,于是紫禁城建立了玻璃作坊。不惜工本。這種“宮”里的玻璃器,價值很高。
收藏周刊:在“四海通達(dá)——海上絲綢之路(中國段)文物聯(lián)展”中,館方曾向我們介紹過羅馬玻璃-薩珊玻璃-伊斯蘭玻璃的流變。公元1-2世紀(jì)的羅馬玻璃盛極一時。西漢張騫出使西域,開通絲綢之路,羅馬玻璃開始傳入中國,如廣州橫枝崗西漢墓葬出現(xiàn)的羅馬玻璃碗。公元3世紀(jì),隨著波斯薩珊王朝的興起,玻璃產(chǎn)業(yè)興旺,薩珊玻璃成為東晉門閥愛物。公元7-8世紀(jì),伊斯蘭玻璃興起并通過海上絲綢之路,傳入中國,“清明無垢”大受青睞。
安家瑤:在我國出土的羅馬玻璃、薩珊玻璃、伊斯蘭玻璃等器物,以及國產(chǎn)玻璃制造技術(shù)的演進(jìn),不僅反映出玻璃器與玻璃技術(shù)是由西向東逐漸傳入中國的,也驗(yàn)證了世界玻璃史的演進(jìn)過程。玻璃雖小,卻能折射出東西文化在絲綢之路上交流碰撞的璀璨光芒,這正如習(xí)近平主席所說,“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鑒而豐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