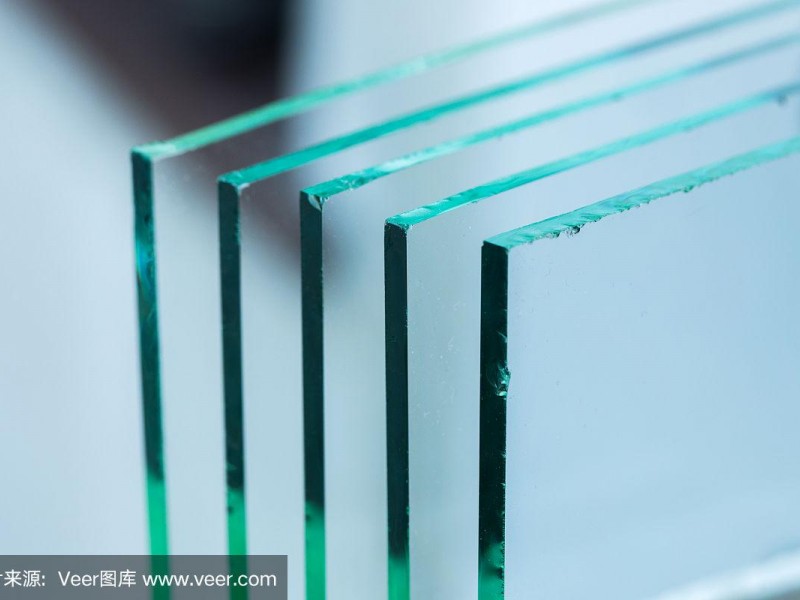玻璃器皿之都祁縣濃濃的玻璃風情:玻璃搭建的微景觀。B06-B07版攝影/新京報記者白華兵

王瀟在玻璃瓶上進行手繪。

展柜里展示的各色高腳杯。

玻璃器皿之都祁縣熱火朝天的玻璃器皿生產車間。
一桌一椅,一個玻璃瓶,勾線、貼花、上色,不一會兒玻璃瓶就在王瀟筆下栩栩如生了。
在玻璃上“作畫”的王瀟從老家貴州茅臺鎮來祁縣工作已18年了,當年他來這兒的時候正趕上祁縣玻璃產業大爆發。不過到現在他還沒有習慣北方的干冷和各種花樣的面食,中午他會到企業專門配備的廚房做一點家鄉口味的飯菜,隨便扒一口,就趕緊回到車間繼續在玻璃上“作畫”。
就是這樣的玻璃器皿,支撐祁縣紅海玻璃每年向阿拉伯地區銷售數千萬元的產品,成了當地的特色產業。
“擁有80年歷史的祁縣玻璃器皿產業從生產兒童玩具、馬燈罩起步,發展到今天酒具、茶具、咖啡具、蠟臺、風燈、水升、果盤、糖盒、花瓶和工藝品等10余個系列8000多個品種,”山西晉中市祁縣玻璃器皿產業發展中心主任胡曉峰介紹,“發展中也有過惡性的競爭、痛苦的徘徊、艱難的調整,近年來漸入佳境。2020年銷售額達到37億元,其中出口3.59億美元,占據全國人工吹制玻璃器皿出口量的一半。”
2012年,祁縣被中國輕工業聯合會授予“中國玻璃器皿之都”稱號。“左手產業,右手藝術,如何拿捏確實是一道難題。”為此,新京報貝殼財經記者深入祁縣,在一盤盤高溫熔爐之間還原這個縣域特色經濟的“藝術與人生”。
傳承
“吹出”的大產業,80后手工匠人成行業主力
“我是18歲初中一畢業就進入玻璃廠的,”看見記者的疑惑,閆傳明趕緊改口,“其實那時剛剛15歲,一開始只能做小工,后來做大工、班組長、車間主任。”
抹了一把汗,閆傳明招呼著記者注意安全,小心燙著。三盤1500多攝氏度的高溫玻璃熔爐成三角形布局,工人挑著滾燙玻璃在中間穿梭,有吹、有滾、有敲、有磨,忙而不亂。
閆傳明進一步解釋,玻璃器皿生產這個行當一般都有十多道工序,每一道技術含量不一樣,需要的工人級別也不同。而從小工到大工,需要經歷多道工序,一開始洗瓶、包裝,干技術含量低的工作,到后來進入生產流程,打小泡、取料、滾料、吹玻璃、拉挺、捏底、靠底、炸口、磨口、烘邊,每一個環節都少不了。
這里是中國玻璃器皿生產中心祁縣大華玻璃的一個普通車間。經過近20年的“跋涉”,閆傳明成了車間主任,他的月工資收入也從三四百元向上突破1.5萬元。
事實上,進玻璃廠工作成了祁縣眾多80后剛步入社會的選擇。1984年出生的郭永興已經是紅海玻璃的車間主任,他16歲進入玻璃廠當小工。喜尊玻璃的車間主任馬鑫鑫15歲入行。而大華玻璃領著高薪的車間管理人員就有12名,大多是85后。
“2000年前后,祁縣玻璃產業大爆發,就連學校里老師批評學生都是‘不好好學習以后就讓你去吹玻璃’。”郭永興回憶。
同樣是小學徒出身,現在已經成功創業的張文磊告訴記者,當初的“80后”紛紛進入玻璃器皿行業是因為2000年前后的祁縣出路并不多,沒有煤炭,進入社會后不去開大車搞運輸,就得進玻璃廠當工人。也正是得益于當時產業的爆發,才使祁縣手工玻璃的傳承沒有出現斷層。曾經只是為了掙點錢養家糊口去吹玻璃的80后,今天已經成了主力軍。
長期從事玻璃營銷策劃和品牌建設的任君燁告訴記者,“一開始祁縣玻璃器皿產業在全國并沒有太多優勢,運城聞喜縣也是重要的玻璃器皿產業聚集區。2000年以后,很多地方玻璃器皿行業因其他產業的發達而人才流失嚴重,最終失去了主陣地。祁縣的玻璃器皿廠家乘勢而為,再加上政府部門的重視,最終走到了今天,迎來全行業崛起。”
胡曉峰表示,玻璃器皿產業在當前發展階段,人工的作用無可替代,也正是對手工技藝的堅持,才使得祁縣玻璃器皿有今天的江湖地位,在這個過程中,成批出現的80后功不可沒。
發展
曾歷經波折,疫情下逆勢而上
走到祁縣的城鄉,迎面而來的是濃濃的玻璃風情。除了玻璃主題公園、玻璃文化藝術中心、以玻璃為主的會展中心,就是星羅棋布的玻璃器皿廠。
祁縣是晉商腹地,老晉商萬里茶路的中心,如今祁縣玻璃器皿遠銷海外正是老晉商精神的延續。在會展中心,胡曉峰經常要向來自全國乃至世界各地的客商推介祁縣的文化和玻璃。
祁縣玻璃器皿產業因出口而興,產品約60%-70%銷往國際市場。其中,美國市場占出口量的50%,歐洲市場占出口量的30%,其余銷往南美、中亞及非洲等市場。這個會展中心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建成的“門臉”。
記者了解到,當初祁縣玻璃器皿的發展并不順利。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后,世界人工吹制玻璃器皿生產中心開始由歐洲向中國轉移,祁縣玻璃抓住了機遇。不到10年時間,全縣玻璃器皿企業增至160戶,年產值由1.5億元增加到14億元,占祁縣工業總產值的30.4%,自營出口額保持年均30%左右的高增長率。
然而,全行業的迅速發展也使得企業小散亂現象嚴重,能耗高、污染嚴重。到2008年,亞洲金融風暴使祁縣玻璃器皿產業出口受挫,再加上環保政策的收緊,調整就此展開,眾多庭院式小廠關門。
到2012年,祁縣玻璃器皿廠縮減到60多家,在政府的主導下,開始產業調整、升級,終于在2015年迎來一個小高峰,產值升至20多億元。2017年受中美貿易摩擦影響,祁縣玻璃器皿產業又陷低谷,企業數量進一步縮減到38家。
此后,進入兩三年的徘徊期。“好像那里卡住了,但又找不到問題。”張文磊坦言。
“是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讓祁縣再一次抓住機會,”如今,回憶那次“搏殺”胡曉峰心有余悸,“2020年初,疫情突然襲來,放假、停產、封爐,玻璃器皿企業被打了個措手不及——要知道那可是1200多攝氏度的高溫,一旦熄爐就意味著報廢,但保溫每天都需要巨額開支——這時候,最需要的是冷靜。不到一個月,我們已經全面復工復產,但國外因為疫情開始封閉。我們當時就組織企業開會研究對策。我們分析認為,疫情的緊急停產應該不會超過兩個月。這兩個月的出貨量,動員貿易商吸納一個月的,動員銀行給企業提供一個月產值的貸款。”
這一次,賭對了。
胡曉峰表示,因為國外疫情持續,恢復生產乏力,大量國外訂單涌入。一年來,祁縣玻璃器皿廠又增加了8家,且家家訂單爆滿,國外商超抓住機會備貨,以防疫情反撲。
困局
祁縣玻璃器皿產業的四道坎
“一個月工資上萬元,這才是有點技術的年輕人本來的樣子,否則養家、供房貸,沒有辦法堅持,”馬鑫鑫告訴記者,他們周邊的同齡人有三四成從事玻璃器皿工作,就算普通大工,現在每個月都能掙到八九千元的工資,每天平均工資300元左右,“畢竟是體力工作,還深處高溫環境,現在的90后、00后壓根不愿意干這一行。”
據當地官方統計,祁縣玻璃行業的直接從業者高達3萬人,缺人、人力成本較高已經成了一個行業性問題。人力成本的上漲和年輕人的遠離,成了玻璃器皿行業的一道坎。
第二道坎則是能源、原材料漲價。
“特殊時期的訂單飽和讓祁縣玻璃器皿產業松了一口氣,但行業面臨的問題并沒有得到解決,”大華玻璃高管王騰憂心忡忡,“人力成本上漲,能源原材料價格也在上漲,唯獨杯子沒有漲價。”
王騰舉例子:一只玻璃杯,十年前的出廠價格是4塊多,現在還是這個價,而市場上的機制玻璃則是9.9元可以買到一盒4只杯子。
記者了解到,1992年創辦的大華玻璃是祁縣玻璃器皿產業中的旗艦,2015年鼎盛時期產值高達4億元,員工達到5000人。與其他玻璃企業強調后續加工不同,大華玻璃專注于“入口玻璃”,要把玻璃杯做到極致。也正因此,他們對國際市場日用玻璃的價格和成本更為敏感。
因此,大華玻璃沒有搶這一輪出口潮,他們關閉了一些產能,把注意力向高端智能制造和低成本的機制玻璃轉移。
胡曉峰表示,產品質量升級是祁縣玻璃器皿產業面臨的第三道坎:“以前的杯子都是高白料,而現在要水晶料,還要無鉛水晶。十年前,杯子上有點氣泡、凹凸、污點、微變形等瑕疵很正常。而現在連普通工人都不好意思面對這樣的杯子。”
記者了解到,在祁縣人心中,玻璃器皿企業有三條路,要么足夠大——像大華玻璃——能夠影響市場;要么延伸服務,做好玻璃器皿的深加工,走特色化的道路;要么就放棄抵抗,去普通消費市場搏殺,或者給大型企業、商超代工。目前,祁縣玻璃器皿生產企業有注冊商標41枚,其中馳名商標只有大華、宏藝2枚。在祁縣人看來,這與他們的地位不匹配。
因此,品牌化成了祁縣玻璃器皿產業的第四道坎。
胡曉峰告訴記者,不僅如此,產業配套、自主營銷、產業規范都十分重要,解決不好就會傷害整個產業。
創新
三面突圍尋找產業新路
“這個杯子是喝汾酒的,這個是喝茅臺(600519)的,這個是喝白蘭地的,這個是喝清酒的……不能混著來,酒具是酒文化的載體,”胡曉峰進一步解釋,“當前,消費升級,輕奢文化被廣泛接受,這給祁縣玻璃器皿提供了廣泛的發展空間。”
輕奢,正是任君燁念念不忘的。因為自己祖輩、父輩都從事玻璃器皿的工作,任君燁把自己說成“第三代玻璃人”。身居廣東,一手牽海外,一手連內地,他的玻璃器皿事業風生水起。任君燁至今無法忘記,一次展會上,當外國客商帶著樣品問他能不能生產,他回答“不能”時,這名客商詫異的表情和自己的尷尬。此后,任君燁先后與多家廠商合作,打造自己“想要的玻璃杯”。
張文磊,2017年他經過18年跋涉,在從小工干到廠長,并且調換多個企業后,“感覺事業走到盡頭”,想著換個跑道。
胡曉峰介紹,當前低端市場幾塊錢的玻璃杯比比皆是,而高端酒店上千元的高腳杯已經被廣泛接受,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現在的很多家庭都需要有這樣的高品位杯子裝扮生活。
這時候,任君燁和張文磊相遇了,他們瞄準高端共同創辦的喜尊玻璃很快上馬。
“創業并沒那么簡單,”張文磊回憶,“投資500萬后,第一年就虧掉200萬。在長期依賴出口的環境中,要去搶占內銷的高端市場首先面臨的是品牌認同。”
對此,任君燁胸有成竹。他在2011年就創立了國內第一個手工水晶杯高端品牌——凱洛詩。
“避開低端市場的廝殺,奪回國內高端市場一直被國外品牌占領的陣地,”胡曉峰解釋,“不是沒有生產高端產品的能力,而是在品牌的支撐下,需要逐步完善營銷體系、文化認同等配套工作。”
在喜尊玻璃的生產車間,一條標語十分醒目:“我們不是工人,我們是工匠,我們是中國玻璃藝術傳承者。”
在紅海玻璃默默做手繪17年的王瀟這樣定位自己:“我不是什么藝術家,就是一名靠手藝吃飯的工匠。”
紅海玻璃一直在工藝玻璃的道路上前行。“一方面鞏固提升祁縣玻璃器皿人工吹制優勢,另一方面發揮手工套色、花挺、混色、熱粘等工藝特長,精品化、特色化、藝術化,闖一條‘文化+產業’的路。”紅海玻璃李建生介紹。
“大華玻璃因為大,注定要走大而穩的路。”負責大華玻璃智能制造項目的段樹盛說,“從去年開始,大華玻璃就在晉中市政府的支持下,開始建設智能制造生產車間。”段樹盛介紹,這個項目總投資達到3.68億元,把人工與機器相結合,標準化、流水線,將會節約90%的人力,同時還能保持人工的品質,是現代產業的發展方向,預計明年8月首期建設完工。
特色、高端、智能制造,在不同賽道上,祁縣玻璃闖出了新路,這將惠及整個行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