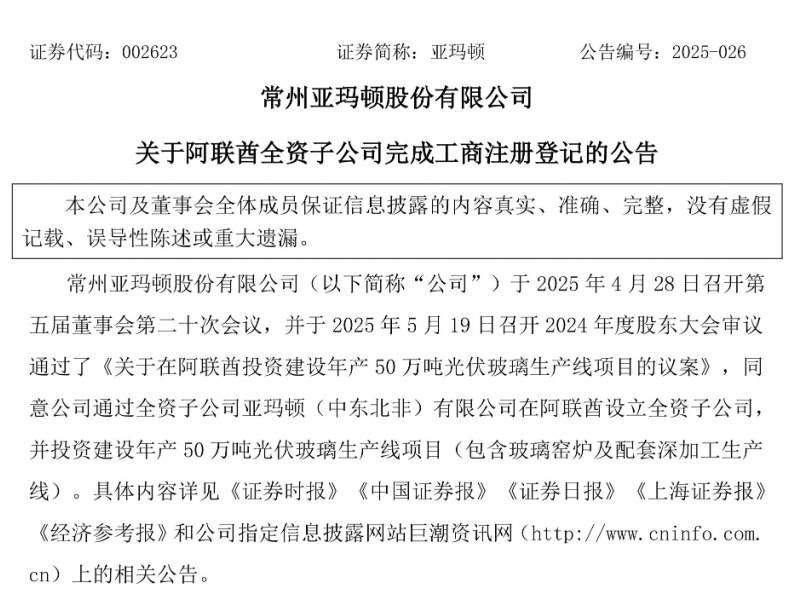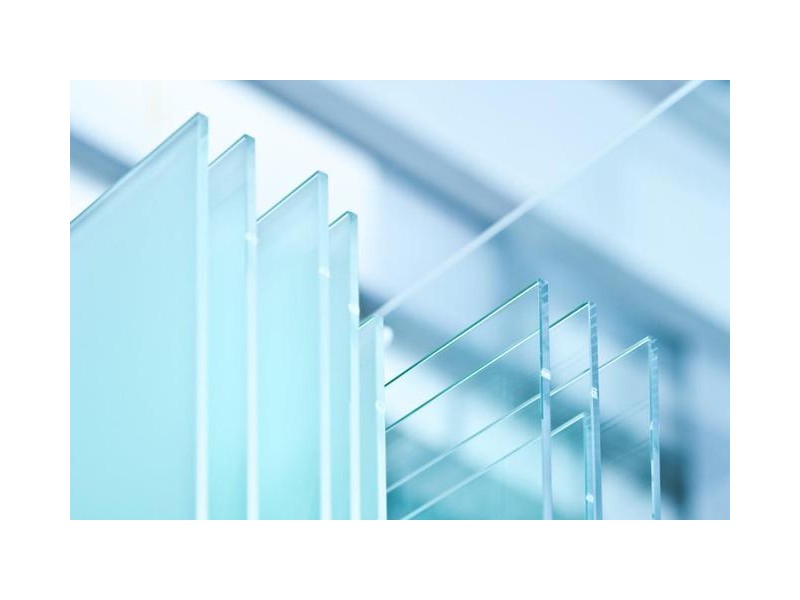從上世紀60年代Studio Glass運動以來,玻璃這一材質越來越多地被運用到當代藝術領域,玻璃藝術也為更多民眾所熟知。繼承這場先鋒藝術運動的第二代玻璃藝術家們成功讓玻璃藝術品列入了各大博物館的收藏清單,這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美國玻璃藝術先驅圖茲·詹斯基(Toots Zynsky),她是第一位被紐約當代藝術館MOMA收藏作品的玻璃藝術家。圖茲·詹斯基那些色彩鮮艷、獨具一格的作品迄今已被全球超過70家博物館收藏。

1月12日,Toots Zynsky帶著她的二十件作品來到上海琉璃藝術博物館,組成由上海琉璃藝術博物館創始人張毅策展的“極光之舞——Toots Zynsky作品展”。“極光之舞”的展覽名源自其中一件作品,紅橙黃綠藍紫各色細如發絲的玻璃絲融合成一件花朵形狀的玻璃容器,張毅說:“第一眼看到這件作品,我就想到了極光在天空流動舞蹈的場景,于是最終為這場展覽命名"極光之舞"。”
藝術之路從來不容易,圖茲·詹斯基并非一開始就找對風格方向。除了玻璃之外她也曾嘗試過影像、鐵絲網等多種創作手法,后來她還是選擇回歸玻璃,并且獨創了熱熔玻璃絲技法。
一次燒制過程中,圖茲·詹斯基偶然地擠捏還未成形的玻璃,發現玻璃擠壓后的形狀竟然十分特別,于是延續了這種似碗似花的造型直到今天。
圖茲·詹斯基衣著家常,笑容親切,半個多小時的對話中,圖茲·詹斯基常常露出一派天真的神情,還興致勃勃地談起“小時候在后院挖洞,被鄰居打趣是不是要挖個隧道去中國”的故事。

記者:你的創作靈感從哪里來?
圖茲·詹斯基:主要是源自個人喜好和生活經歷。我喜歡鮮花,從小我就只要鮮花做生日禮物,而不是玩具。鮮花中最喜歡郁金香和水仙。荷蘭是花的天堂,我曾經在那里住過一段時間,每天都在屋里擺滿花。所以我的很多作品都形似花朵,色彩艷麗。曾祖母留下的針織品,那些五彩的絲線讓我著迷,她給我的影響直到多年后才在我的作品中體現出來。
記者:你是如何研發出熱熔玻璃法的?
圖茲·詹斯基:玻璃有很多特性吸引我。比如它很易碎,雖然易碎給創作帶來難度,但同時也帶來了無限的可能。如果連這一點挑戰都沒有,創作過程就沒那么刺激好玩了。除此之外,玻璃還可以永久保持色彩。最開始做玻璃作品時,我只是常規地吹制,這個過程必須非常快,不然玻璃就會凝固。后來我慢慢發現,如果快速旋轉,玻璃就可以被拉成細絲,雖然剛開始拉出的絲粗細不均,但我仍然很激動,這讓我想起曾祖母的針織品上那些縱橫的絲線。之前我一直是手工拉制,效率很低,后來在一位荷蘭朋友的幫助下,我們造了一臺專門的機器,每天可以拉出大量均勻的細絲,為創作提供了足夠的材料。
記者:戴爾·奇佛利(Dale Chihuly)是Studio Glass運動的推動者,他是如何影響你的?
圖茲·詹斯基:戴爾是非常有魅力的人,也吸引了一大批志同道合的人在身邊。我是他的學生。但玻璃藝術的進步也仰賴歐洲和中國藝術家們的共同努力。當時,我們做了很多試驗性的東西,用玻璃完成了很多瘋狂的想法。直到二十世紀,玻璃才被用作獨立藝術家的創作媒介,總之,對我而言那是一段激情歲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