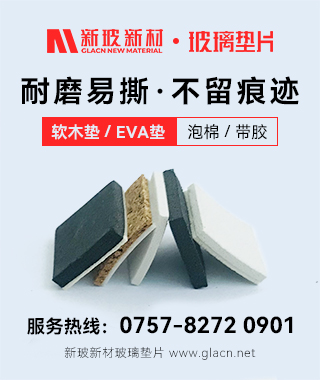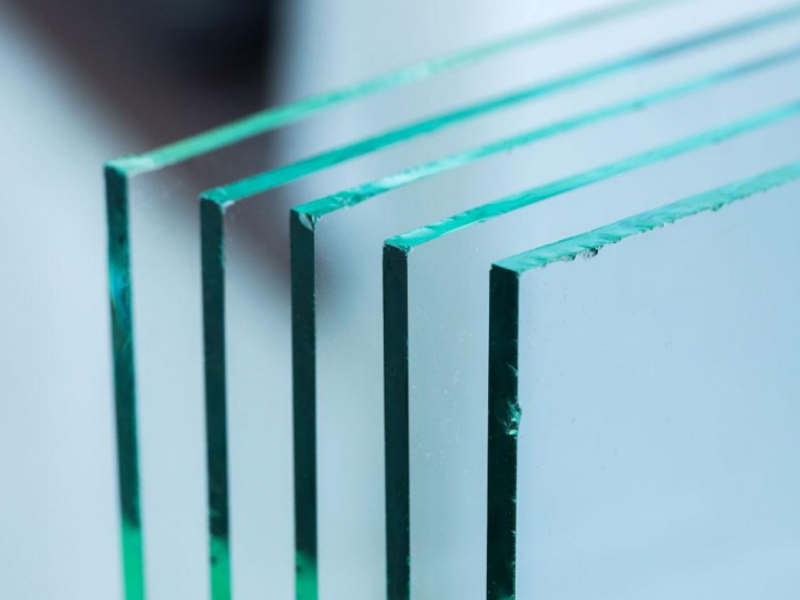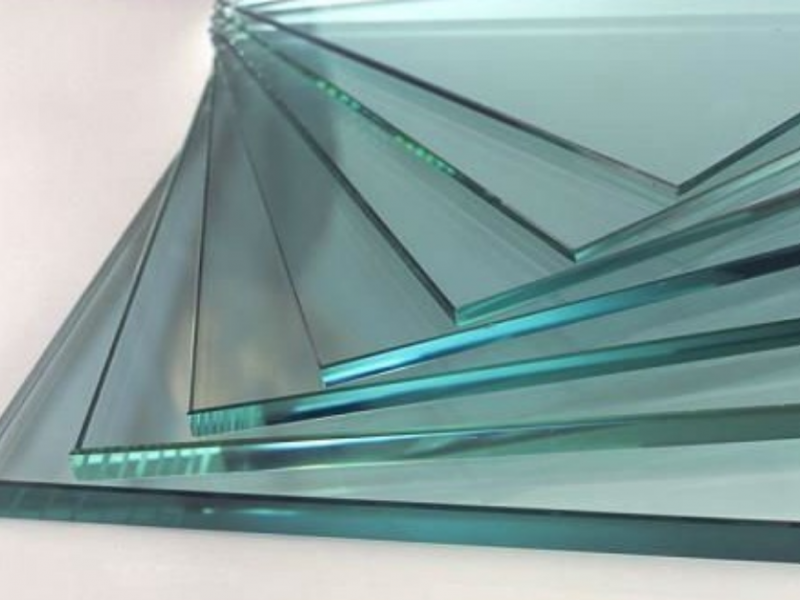講座的開始,彭怡解釋到之所以使用“什么東西”作為講座的名字,不僅是因為其中包含的“東西方”的含義,也因為她常常被人問到燈工玻璃究竟是“什么東西”。在進入對燈工玻璃的介紹之前,彭怡先簡要介紹了鑄造玻璃工藝、吹制玻璃工藝、鑲嵌玻璃工藝、玻璃冷加工工藝和近幾年時興的水刀切割工藝、玻璃絲網印刷與熱熔工藝、玻璃絲網印刷與玻璃粉成型工藝。
隨后,她以不同藝術家的燈工玻璃藝術作品為例來介紹燈工玻璃工藝——用玻璃棒或玻璃管在噴槍的火焰上加熱而后用不同工具進行塑形的工藝。意大利藝術家Cesare Toffolo利用玻璃棒制作了很多小人物,并使用輔助的工具給小人加上眉毛眼睛,創作了小人與吹制玻璃器具結合而成的藝術作品。意大利威尼斯的穆拉諾是一個在歷史上以玻璃工藝聞名的小島,來自于此的藝術家的作品是將傳統與現代結合的典范。在彭怡隨后的介紹中,十分具有現代性的美國藝術家David Wills利用燈工玻璃工藝做出精細的小花,幾乎與真花無異。瑞士藝術家Julie Anne Denton用燈工玻璃制成的小雕塑,然后將之放到沙鑄的模具中再澆上玻璃漿,將燈工玻璃工藝與沙鑄玻璃工藝結合。
彭怡認為燈工玻璃是一種可小可大的工藝,不光可以對玻璃絲進行編織或進行極精細的的塑造,也可以創作大型的藝術作品,如德國藝術家Susan Uebold 將燈工玻璃與燈光結合,作品尺幅巨大。美國藝術家Carrie Feitig曾在英國桑德蘭大學進行交流學習,醞釀于這段時間的作品《家》中,她以玻璃制成許多長達一米長的羽毛懸置于空中,彭怡認為這件作品表達了對信仰的追求,是獨特的西方文化的體現。
彭怡提到自己非常想向大家介紹的一位藝術家是荷蘭的Krista,這是一位接觸燈工玻璃藝術時間很短的藝術家,他用極其簡單的工藝重復制作了成百上千個玻璃小棒,然后將之粘在作品上,產生了十分漂亮的效果,這個作品也被歐洲玻璃博物館收藏。彭怡談到,自己曾與她討論過一個一直困擾自身的問題:“玻璃對于藝術家而言究竟有什么特殊的意義?即為什么要使用玻璃來創作作品?”就這個問題彭怡曾詢問過許多人,將燈工玻璃與霓虹燈結合的美國藝術家Sarah Blood曾回答道,她并不認為自己是“燈工玻璃藝術家”,而只是一個“藝術家”在使用不同材料而已。而Krista的回答十分耐人尋味,她認為并不是自己選擇了玻璃,而是玻璃選擇了自己。她認為做玻璃的人身上有著一種特質,甚至認為自己與彭怡是有著相似性格的“玻璃人”,所以這是一種自然而然的選擇。
之后彭怡簡單介紹了亞洲藝術家的作品,如在韓國、日本等地的藝術家用玻璃做首飾設計,用玻璃做成細菌的形象來表示時間,用玻璃來寫詩等等。而在中國傳統中,玻璃常常被做成動物、植物盆景或玻璃珠子、鼻煙壺等。中國以玻璃為材料的藝術家有孫鳳軍、馮平生、周毅、鄭文卿、黃然、楊碧琪等等。
講座的最后一部分,彭怡介紹了自己在英國留學期間的玻璃藝術作品及其中的文化意義。如她在本科時所創作的作品《茶壺》,她說到,在英國時自己十分想念中國文化,迫切的想要使用中國元素。她認為現代文化是東西方結合的,我們既可以喝可樂也可以喝茶,所以她將可樂瓶等的形象與中國茶壺的形象結合起來。2008年她的《可樂茶壺系列》依然沿用可樂瓶的外形,并使用了吹制玻璃工藝,也體驗了吹制玻璃工藝的困難。在《算盤鍵盤》這件作品中,她制作了鍵盤的外形,卻利用絲網印刷將字母印刷到每一顆算珠上,使每一顆算珠成為鍵盤按鍵的模樣。這些都體現了她對東西方文化的思考,正如她的博士課題——“跨文化燈工玻璃藝術——在東西方文化背景影響下創意運用燈工玻璃工藝到當代玻璃藝術中”。在《解構》中,她將中國市場上常見的鼻煙壺進行切割,又將其重組,象征了文化的丟失與回歸。此外,她還將北京梨園料器場的廢棄料器與宜家的玻璃杯子結合,創作了一系列作品,象征了工業生產與古老文化的碰撞。彭怡最后提到一個正在做的項目,即每個人制作一片玻璃葉子,通過對此的收集,變成蜿蜒的玻璃藤蔓,成為一件能夠一直延續下去的玻璃藝術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