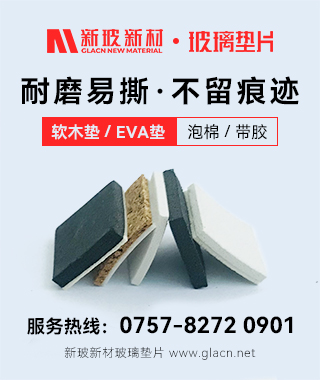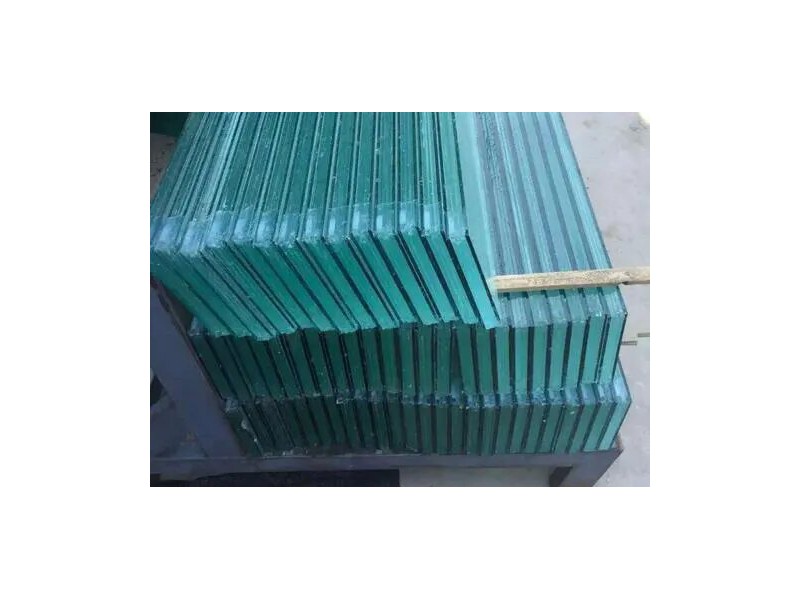杜蒙制作的玻璃藝術品。
玻璃吹制工作室內,杜蒙往脖子上草草扎了條毛巾。略顯瘦弱的她雙手舉著一根2米左右的不銹鋼吹管,熟練地從1300℃的熔爐里挑出一團糖漿般黏稠的玻璃原料勻速轉動著。
盡管通著風,屋內放置的溫度計數字依舊頂到了頭。杜蒙說,在雨天,T恤衫甚至能在干完活后擰出水。
“玻璃既像是我的孩子,也像一位‘相愛相殺’的老朋友。在不了解玻璃性格的時候,很容易和它‘較勁’。”這個年輕的北京姑娘,馬上就要迎來她與玻璃朝夕相處的第十個年頭。

杜蒙制作的玻璃藝術品。
杜蒙的每一件作品都像在講一個生動的故事:無論是抱著兔子的小女孩,還是花叢間盤臥的小鹿,作品中的角色都像是從童話中走出來一般。
精巧的工藝讓人很難想象,這些作品出自一個“半路出家”的藝術家之手。
2008年,在玻璃藝術家戴爾·奇胡利的一次大型個展上,當看到玻璃制成的藝術品折射出的美妙光影時,杜蒙立即被這種像是“來自外星球的神秘藝術”震撼了,并由此做出了一個決定——學習玻璃制作。
為此,此前毫無玻璃制作背景的她開始大量查閱相關知識,并試著申請了幾所院校,最終被美國羅切斯特理工學院玻璃專業錄取,成為該碩士項目招收的第一個中國學生。

工作時的杜蒙。
然而,對玻璃制作僅有想象的杜蒙剛入校,就遇到巨大困難。在專業領域,她不僅被同班同學遠遠甩開,甚至和本科二年級學生的水平也相差甚遠。不斷制作、不斷失敗,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杜蒙拿這門看似簡單、實際操作難度極高的工藝毫無辦法。體型嬌小的她形容,每次吹完玻璃體力都急劇透支,“就像被‘毒打’過一般”。
“玻璃這門技藝不存在任何捷徑。細微的天氣變化、一秒的誤差都可能導致它的碎裂。”面對難以逾越的鴻溝,她第一次后悔學習這個專業。假期回國時,她甚至萌生了退掉返程機票的念頭。
“但我又想,如果真退了,將來可能會因為沒有盡全力嘗試而后悔。”杜蒙咬牙回了學校。她慢慢找到了自己的節奏,也逐漸習慣了玻璃帶給她的“傷害”。
一次運料時,崩碎生料的尖角扎進了她的膝蓋。正在干活的杜蒙毫無察覺,直到從工坊出來,同學都盯著她的膝蓋看時,她才意識到發生了什么。處理傷口的時候,整條褲管已經被血粘在了腿上,脫都脫不下來。
“這就是我們專業的畫風:衣服上總有燒破的洞,身上粘著創可貼。”她笑著說,現在家里的藥箱還備著各種燙傷藥。

杜蒙制作的玻璃藝術品。
像是表達自己學做玻璃以來的狀態一般,學期末,杜蒙做出了一組低著頭的小女孩的作品,得到同學們一致認可。將杜蒙的經歷都看在眼里的教授為此寫了一封真摯的郵件,肯定了她的進步,這讓她當即淚如雨下。
回憶起與玻璃相處的點點滴滴,杜蒙說:“我一直挺愛玻璃的。它脾氣挺大,但做得越多越了解它。”
2018年,在全球玻璃界享有盛名的玻璃藝術協會論壇上,杜蒙獲頒“新銳藝術家”稱號。在此之前,此稱號幾十年間無中國人獲得。

杜蒙制作的玻璃藝術品。
曾有觀眾在參觀杜蒙的作品后特意找到她,傾訴自己的故事,感謝她的創作。這讓她覺得很溫暖。
“我也曾做過很多關于北京的作品,比如小時候的小白鞋和飛過天空的燕子,來留住自己對家鄉的記憶。”杜蒙很喜歡這種用藝術溝通的方式,“如果我的作品能觸摸到你心中某一個柔軟的點,就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