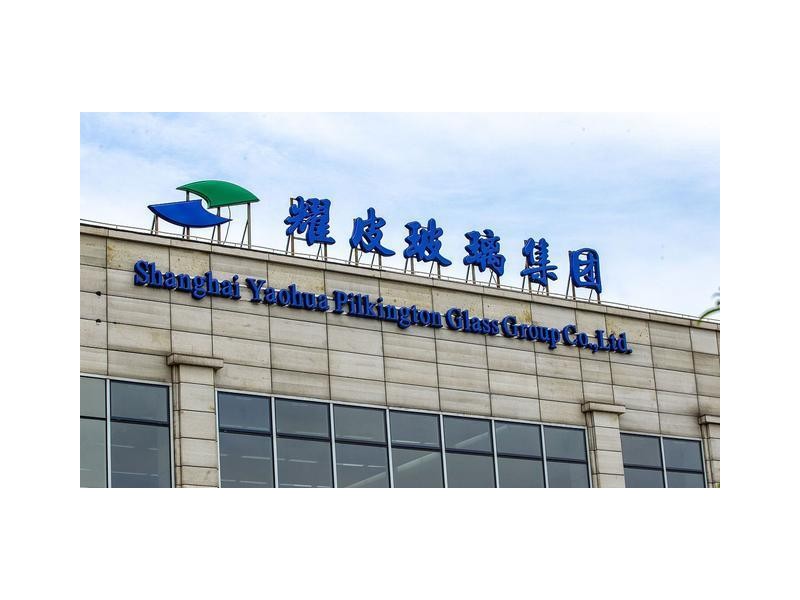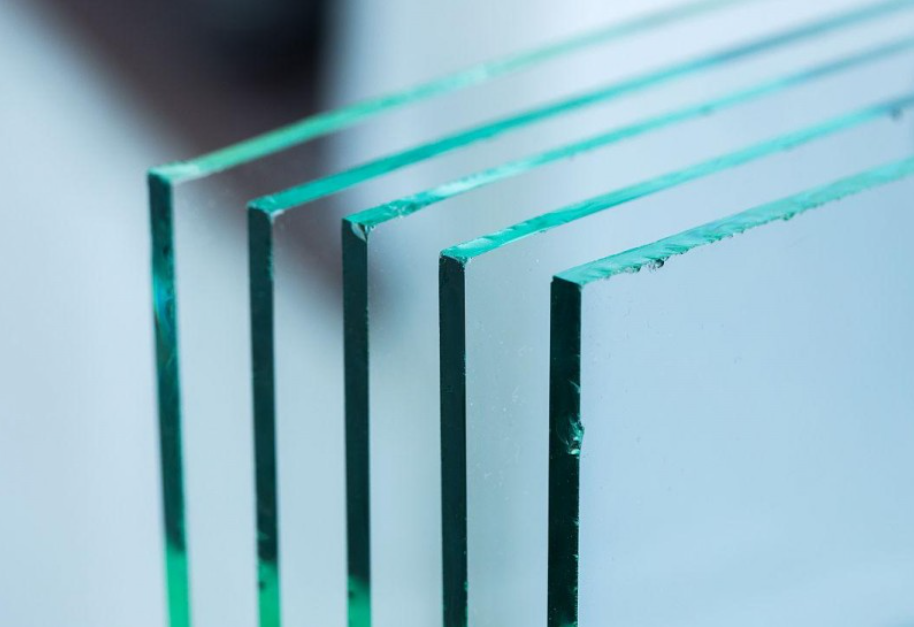在威尼斯北部、離主島大約1.5公里處,有個(gè)叫穆拉諾島的地方。它由五個(gè)島組成,總共人口不到1萬,更多人叫它“玻璃島”。相傳在1291年,威尼斯政府為避免玻璃爐火引燃大面積的木制房屋,下令所有玻璃廠遷往穆拉諾島,同時(shí)禁止玻璃師們離開威尼斯,這是“玻璃島”最早的雛形。14世紀(jì)以后,威尼斯商人那里出口玻璃制品,比如玻璃珠、玻璃鏡子等;到了16世紀(jì),玻璃師開始研制水晶玻璃、金絲玻璃、仿寶石玻璃和彩色玻璃,豐富的工藝為威尼斯帶來巨大的財(cái)富。
如今,“玻璃島”是威尼斯重要的旅游景點(diǎn),但在藝術(shù)史上,它的意義絕非僅此:原本陶藝出身的“玻璃藝術(shù)之父” Harvey Littleton,正是因?yàn)樽咴L了該島上的50多家玻璃廠,才開始投身玻璃創(chuàng)作和研究,并推動(dòng)“玻璃藝術(shù)工作室運(yùn)動(dòng)”:1962年,他在托萊多藝術(shù)博物館建造了第一個(gè)玻璃吹制車間,藝術(shù)家們可以走進(jìn)工作室,用小型玻璃熔爐完成作品。此舉不僅解放了玻璃材料的藝術(shù)邊界,也催生出不少高校的玻璃項(xiàng)目,如威斯康星大學(xué)、加利福利亞藝術(shù)學(xué)院、羅德島設(shè)計(jì)學(xué)院等。不完全統(tǒng)計(jì),一些重要的當(dāng)代玻璃藝術(shù)家,如 Dale Chihuly(美國)、Stanislav Libensky和 Jaroslava Brychtova(捷克)、Livio Seguso(意大利)和藤田喬平(日本)都曾受其影響。
說到這兒,你可能也發(fā)現(xiàn)了:“玩”玻璃,還是老外“玩”得久。
中國當(dāng)代藝術(shù)和玻璃工藝會(huì)碰撞哪些火花呢?
由上海玻璃博物館發(fā)起的項(xiàng)目“退火”正試圖給出答案。過去兩年,藝術(shù)家張鼎、楊心廣、廖斐分別用玻璃完成“黑色物質(zhì)”、《玻璃腸》與《平坦》。今年,參與此項(xiàng)目的藝術(shù)家是林天苗和畢蓉蓉,她們將在今年年底展示新作。


上海玻璃博物館內(nèi)景
退火
“原本以為挺有把握了,但事實(shí)上沒有我想象的那么簡單,現(xiàn)在才摸到一點(diǎn)邊。”林天苗感嘆。過去一個(gè)月,她和工程師們走訪了上海和周邊地區(qū)大大小小的玻璃廠,接觸到玻璃材質(zhì)“無邊的可能性”。每次接觸新的物料和玻璃制作工藝,她的方案可能就會(huì)改變。“最初的幾個(gè)方案,已經(jīng)消失了。”
“玻璃材質(zhì)涉及的問題太廣了。”林天苗羅列了以下問題:如果玻璃里承載液體,那么液體的流動(dòng)的速度和方向怎么處理?液體的粘稠度如何控制?不同玻璃的透明度及顏色有哪些可能性?如果涉及燈、電流、機(jī)械轉(zhuǎn)動(dòng)、影像等,玻璃和它們關(guān)系是怎樣的……當(dāng)然,這些問題只是冰山一角。“好幾次回到博物館就快睡著了,想到一個(gè)新的點(diǎn)子,又蹦起來記下來。”林天苗說。
事實(shí)上,每一位參與“退火”的當(dāng)代藝術(shù)家都曾經(jīng)歷過這樣高強(qiáng)度的調(diào)研。“玻璃工藝很復(fù)雜,當(dāng)代藝術(shù)家很少有機(jī)會(huì)去花時(shí)間了解玻璃工藝,所以作品正式創(chuàng)作前,我們會(huì)帶藝術(shù)家跑工廠。我們提供各類材料和技術(shù)的支持,讓藝術(shù)家們能夠盡可能的實(shí)現(xiàn)每一個(gè)方案。”上海玻璃博物館館長張琳說。
2013年,張琳拜訪了穆拉諾島上的Berengo畫廊,該畫廊與全球當(dāng)代藝術(shù)家都有緊密的合作,這令他冒出想法:為何不讓玻璃跨界當(dāng)代藝術(shù)?
“說實(shí)話,我之前并不了解當(dāng)代藝術(shù)。所以,我找到了朋友李力,請她當(dāng)策展人,來選擇合適的藝術(shù)家。”張琳還記得香格納畫廊創(chuàng)始人何浦林第一次來玻璃博物館的場景,“勞倫斯參觀了以后,對玻璃很感興趣,很快地就答應(yīng)了。”

張鼎《黑色物質(zhì)》2014-2015 126×126×126cm 黑色玻璃, 氧化鋼板


楊心廣的《玻璃腸》方案圖 (圖片由上海玻璃博物館提供)

上海玻璃博物館內(nèi)景 2016“退火”展覽現(xiàn)場 圖為楊心廣的《玻璃腸》(圖片由上海玻璃博物館提供)
2015年,上海玻璃博物館舉辦張鼎個(gè)展“黑色物質(zhì)”。在張鼎的作品中,那些黑色的、看不清內(nèi)部的玻璃球,既表達(dá)出玻璃堅(jiān)硬、通透卻致密的物理性,同時(shí)傳達(dá)力的作用:它們既支撐著每一層的黑色平面,也為其中保留了輕盈的空間。2016年,該項(xiàng)目正式命名“退火”,廖斐和楊心廣汲取了玻璃不同的特性,完成截然不同的作品:楊心廣的作品《玻璃腸》不大,每一顆玻璃球整齊連接成一條曲線,表現(xiàn)了玻璃小巧、精致卻堅(jiān)韌的一面;廖斐的《平坦》則借助玻璃的平滑、規(guī)整、透明的屬性,藝術(shù)家以疊加的形式,打造出和觀眾、和光線、和場館的互動(dòng)性。
“玻璃可以璀璨華麗、宏大、沉重;它同樣也可以很個(gè)性、脆弱、敏感,表達(dá)很私密的情感,玻璃方向性非常豐富。”林天苗說。
由于“黑色物質(zhì)”的順利舉辦,上海玻璃博物館已決定,將“退火”作為常設(shè)項(xiàng)目,每年邀請兩位藝術(shù)家參與,其作品將作為館藏保留下來。“如果說,第一次跨界是一個(gè)單獨(dú)項(xiàng)目,那現(xiàn)在,我們更明確了自己的目標(biāo)。我們要建立當(dāng)代藝術(shù)的館藏。”張琳說,為此,他已簽下“退火”的五年協(xié)議,目前已初步確認(rèn)參展藝術(shù)家。
據(jù)館方公布的數(shù)據(jù)顯示,截至2015年12月31日,上海玻璃博物館自有藏品896件,其中,中國古玻璃藏品29件、西方古玻璃藏品33件;當(dāng)代藝術(shù)品(設(shè)計(jì)作品) 356件;紙質(zhì)藏品18件,玻璃器皿460件。“退火”的合作藝術(shù)家,將為了館方填補(bǔ)“當(dāng)代藝術(shù)”館藏的空白。

廖斐作品《平坦》概念圖 (圖片由上海玻璃博物館提供)
玻璃,能否成為當(dāng)代藝術(shù)新語言?
玻璃作為日常材料,卻很少在國內(nèi)當(dāng)代藝術(shù)領(lǐng)域使用;國內(nèi)外玻璃大師的作品,也主要以視覺傳達(dá)為主,偏向設(shè)計(jì)和工藝。
有著豐富藝術(shù)創(chuàng)作經(jīng)驗(yàn)的林天苗也坦言:“在參與‘退火’之前,幾乎沒有接觸過玻璃。”
據(jù)林天苗和張琳總結(jié),造成這類局面的原因,大致有三個(gè):首先,玻璃工藝復(fù)雜,藝術(shù)家難以在短期內(nèi)充分掌握;其次,不同玻璃、工藝造價(jià)不同,部分大型作品的制作周期以年為單位計(jì)算;再次,在文化領(lǐng)域,玻璃被視為工藝美術(shù),它與當(dāng)代藝術(shù)強(qiáng)調(diào)的思想性和哲學(xué)性相左。
此次協(xié)助林天苗“退火”項(xiàng)目的葉睿雋舉例說明玻璃工藝的復(fù)雜性。“玻璃工藝大致分熱工藝、冷工藝,主要的熱工藝有鑄造和燈工,冷工藝有切割和打磨。每一種工藝的用途和效果都不一樣:鑄造通常用于制作大件,燈工多用來做精美的小件。目前,很少有工廠同時(shí)精通熱工藝和冷工藝,所以要調(diào)研很多廠家。另外,即使是同一種工藝,不同廠家做出的效果也不同,有些表面相對精致,有些比較粗放和概念化。藝術(shù)家要根據(jù)作品的規(guī)劃,選擇最合適的。”
與此同時(shí),玻璃材料也突破了藝術(shù)家常有的創(chuàng)作經(jīng)驗(yàn)。林天苗告訴記者:“想要用玻璃,就必須制定最精確的方案,差一毫米都不行。上次看到一個(gè)玻璃球,單價(jià)造價(jià)30萬,制作工期要一年。我馬上就要反應(yīng)能不能(通過)打孔等技術(shù),來節(jié)省成本和制作周期。”林天苗說,遇上玻璃,她也有“必須妥協(xié)的時(shí)候”。


上海玻璃博物館內(nèi)景 2016“退火”展覽現(xiàn)場 圖為廖斐作品《平坦》(圖片由上海玻璃博物館提供)
不過,最令林天苗觸動(dòng)的,還人們對于玻璃的認(rèn)知局限:“中國傳統(tǒng)陶瓷文化很大程度上代替了玻璃文化的發(fā)展。現(xiàn)代文化中,(我們)把玻璃看作工藝美術(shù)的范疇,當(dāng)代藝術(shù)比較摒棄工藝性。不過實(shí)際上,當(dāng)代藝術(shù)是沒有邊界的,玻璃的可能性也是無邊的。”
目前,玻璃藝術(shù)的學(xué)術(shù)話語權(quán)主要在西方,僅美國就有紐約康寧玻璃博物館、華盛頓玻璃博物館和托萊多藝術(shù)博物館等。其中,康寧玻璃博物館于2015年已開設(shè)“當(dāng)代藝術(shù)與設(shè)計(jì)新館”,新館容納了26000平方英尺的作品展示空間,以及可容納500人同時(shí)觀看熱玻璃表演的劇場。7年里走訪8次康寧博物館的張琳表示,海外玻璃博物館體系已很完善,目前,讓玻璃跨界當(dāng)代藝術(shù)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幾種:一是采取項(xiàng)目合作,館方或提供項(xiàng)目經(jīng)費(fèi)、玻璃原料和工藝支持,作品由藝術(shù)家完成。根據(jù)雙方不同的需求,它可以是商業(yè)合作,也可以作為館藏保留;二是館方建立收藏團(tuán)隊(duì),直接在全球網(wǎng)絡(luò)購買玻璃作品。
對此,林天苗表示,國內(nèi)外藝術(shù)家處理玻璃藝術(shù)的側(cè)重點(diǎn)各有所長:“國際上,很多藝術(shù)家是從設(shè)計(jì)以及高超工藝水平的角度去詮釋玻璃,新的設(shè)計(jì)館就是很好的實(shí)例,這取決于西方成熟的玻璃產(chǎn)業(yè)鏈。而國內(nèi)當(dāng)代藝術(shù)家要將工藝性和思想性恰到好處地結(jié)合在一起,讓當(dāng)代作品既有很強(qiáng)的觀念又有新美學(xué)的視覺,是很難做到的,但它是可以‘取勝’的地方。”

藝術(shù)家林天苗(圖片由上海玻璃博物館提供)
對話林天苗:
“退火”打開我另一種工作狀態(tài)
記者:是什么契機(jī)讓您了解并參與“退火”項(xiàng)目?
林天苗:主要有兩個(gè)原因。
我一直對工藝性的材料如何和當(dāng)代藝術(shù)相結(jié)合感興趣,尤其是玻璃是一種即古老又當(dāng)代的材料,很誘惑我,當(dāng)策展人李力邀請我參與“退火”項(xiàng)目,我把手頭所有項(xiàng)目統(tǒng)統(tǒng)放下,清零思緒滿懷激情地全心投入進(jìn)來了。
另外,我兒子王上做“中國私立美術(shù)館-獨(dú)立調(diào)查訪談”,采訪了上海玻璃博物館館長張琳,看過他的長達(dá)兩萬文字口述采訪,了解到玻璃博物館是用長期、透明做公益事業(yè)的理念去做博物館,能把運(yùn)營情況、組建關(guān)系和財(cái)務(wù)報(bào)表透明地放在網(wǎng)上,在國內(nèi)是很少見的,被博物館健康的運(yùn)用模式而感動(dòng)。同時(shí)被他們?yōu)閯?chuàng)造性的實(shí)現(xiàn)每個(gè)展覽內(nèi)容的工作激情、頑強(qiáng)精神和國家水準(zhǔn)的要求而感動(dòng)。這恰恰與整體社會(huì)好大喜功、虛夸短視的風(fēng)氣和心態(tài),形成鮮明對比和反差,讓我看到美術(shù)館事業(yè)健康發(fā)展的希望。
記者:您目前的方案是什么?
林天苗:最近去過很多工廠,看不同的玻璃工藝的可能性,具體實(shí)施方案一直在變化中。
但作品觀念總體方向沒大變化,總是圍繞著生命本體的“自轉(zhuǎn)”,以及和它所處的社會(huì)、政治、環(huán)境、文化等領(lǐng)域的“公轉(zhuǎn)”規(guī)律去思考,強(qiáng)調(diào)“自轉(zhuǎn)”與“公轉(zhuǎn)”在作品中的“相遇”,在二者相互“凝視”、“了解”的過程中,更容易辨認(rèn)自身的需求和欲望,進(jìn)而把我們的主體意識(shí)變成客體意識(shí),又由“客體”意識(shí)變回“主體”,模擬生命體驗(yàn)。
記者:您的方案為什么一直在變?
林天苗:由于工藝的不同,實(shí)施的可能性一直在變化。過去一年一直在和玻璃博物館溝通,原本覺得自己挺有把握了,但發(fā)現(xiàn)遠(yuǎn)不是我想象的簡單。
液體的流動(dòng)的速度、方向?液體的粘稠度如何控制?不同玻璃的透明度及顏色有哪些可能性?涉及燈、玻璃、電流、機(jī)械轉(zhuǎn)動(dòng)、影像等等很多關(guān)系,總之,涉及的問題實(shí)在太廣了。
面對我的問題,工程師們的反應(yīng)也很有趣,我能從他們眼中看到猶豫,一位廠長說“可能吧?”“我們可能?或者?”這樣的話,我總是說“請你回答yes or no,千萬別猶豫”,他被我直接逗樂了。
另外,就算把所有技術(shù)問題都想清楚了,還要看看項(xiàng)目的預(yù)算,我看到過一個(gè)玻璃球,單個(gè)造價(jià)30萬,而且要花一年的時(shí)間制作,是必須的退火工藝要求,我馬上就要反應(yīng)能不能(通過)打孔等技術(shù),來節(jié)省成本和制作周期。
總之會(huì)發(fā)現(xiàn),這是整個(gè)團(tuán)隊(duì)一起的合作,不同領(lǐng)域的工程師也會(huì)相互爭論,他們聲音大,又用上海話說,我上海話不靈,就只能聽他們講。這一個(gè)月,我基本天天這樣過的,非常興奮,晚上回到博物館馬上就改方案,工作強(qiáng)度和思考的密度非常大,即使如此,我也才剛剛摸到了門。
記者:遇到玻璃這種材質(zhì),您需要“妥協(xié)”的部分,比往常多一些?
林天苗:多太多了,我最開始的那幾個(gè)方案,基本上就都消失了。前幾天,一些老工程師看到第一個(gè)方案時(shí),依然覺得它非常好。妥協(xié)有的時(shí)候讓你很心痛,但沒有辦法必須舍棄。
玻璃是沒有邊界的,它考驗(yàn)藝術(shù)家的綜合能力
記者:您之前有過用玻璃實(shí)現(xiàn)作品的經(jīng)驗(yàn)嗎?
林天苗:之前基本上沒有接觸過玻璃,在兩年前,我就逐步對機(jī)械傳動(dòng)和生命體的規(guī)律性感興趣,并一直推進(jìn)此類型的作品,只是我用的是以前比較容易改變的材料。但玻璃和它們不同,想要用玻璃,就必須在制定最精確的方案,差一毫米都不行。我一旦有新的想法,就要跳起來馬上改,否則這個(gè)想法就會(huì)消失。
記者:如何看待玻璃這種材質(zhì)?
林天苗:它可以璀璨華麗、宏大、沉重;它同樣也可以很個(gè)性、脆弱、敏感,表達(dá)很私密的情感,玻璃方向性非常豐富。使用玻璃的確考驗(yàn)藝術(shù)家開放的觀念、思想的深度,以及整體的控制、實(shí)施、整合、綜合的能力,同時(shí)耐心、韌性也是必不可少的。玻璃的可能性太大了,但正因?yàn)樗鼪]有邊界,會(huì)讓你迷失,你要控制好你自己。
記者:玻璃工藝非常復(fù)雜,大體分為熱工藝(鑄造、燈工)、冷工藝(切割、打磨),每種工藝能達(dá)到不同的效果,您準(zhǔn)備用哪些工藝?
林天苗:我可以在一個(gè)作品里用上所有的工藝,也可以完全都放棄,手段不是特別重要,最重要的是怎么能讓它表達(dá)你最初的一個(gè)觀念想法,控制力和實(shí)施力是非常考驗(yàn)藝術(shù)家的。
藝術(shù)家以思想性去“玩”玻璃
記者:目前,國內(nèi)使用玻璃來實(shí)現(xiàn)作品的當(dāng)代藝術(shù)家并不多。玻璃更被用于制作一些設(shè)計(jì)品和工藝品。您認(rèn)為,這其中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林天苗:中國傳統(tǒng)陶瓷文化很大程度上代替了玻璃文化的發(fā)展。在現(xiàn)代文化中,又把玻璃看作是工藝美術(shù)的范疇,當(dāng)代藝術(shù)強(qiáng)調(diào)思想性和哲學(xué)性,比較摒棄工藝性,所以,當(dāng)代藝術(shù)對玻璃材料的使用也比較少。
國際上,很多藝術(shù)家是從設(shè)計(jì)以及高超工藝水平的角度去詮釋玻璃,新的設(shè)計(jì)館就是很好的實(shí)例,這取決于西方成熟的玻璃產(chǎn)業(yè)鏈。目前,國內(nèi)很少能夠達(dá)到作品需求的工作坊或工廠。
當(dāng)代藝術(shù)家將工藝性和思想性恰到好處地結(jié)合在一起,讓當(dāng)代作品既有很強(qiáng)的觀念又有新美學(xué)的視覺,是很難做到的。一旦“迷上”玻璃這種材質(zhì),不斷探索它的工藝可能性,忘記做作品觀念的初衷,會(huì)被它帶“坑里”的。
記者:藝術(shù)家們對玻璃的認(rèn)識(shí),是否存在很多的空間?
林天苗:有無邊無際的空間,寬闊的方向。西方有很多藝術(shù)家強(qiáng)調(diào)工藝性,比如表現(xiàn)材質(zhì)本身的華麗、漂亮、璀璨、細(xì)膩,但可能會(huì)陷入追求玻璃工藝的怪圈里。我們對玻璃工藝性的把握不占優(yōu)勢,但我們更強(qiáng)調(diào)思想性,它能打破了我們對玻璃材質(zhì)的慣性思考,可能會(huì)有更多“遙遠(yuǎn)”的嫁接,會(huì)產(chǎn)生有意想不到的結(jié)果。
記者:您認(rèn)為,當(dāng)代藝術(shù)遇到玻璃工藝會(huì)產(chǎn)生哪些可能性?
林天苗:可能性是沒有邊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