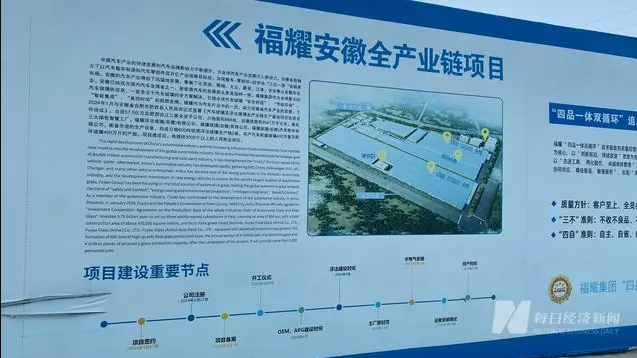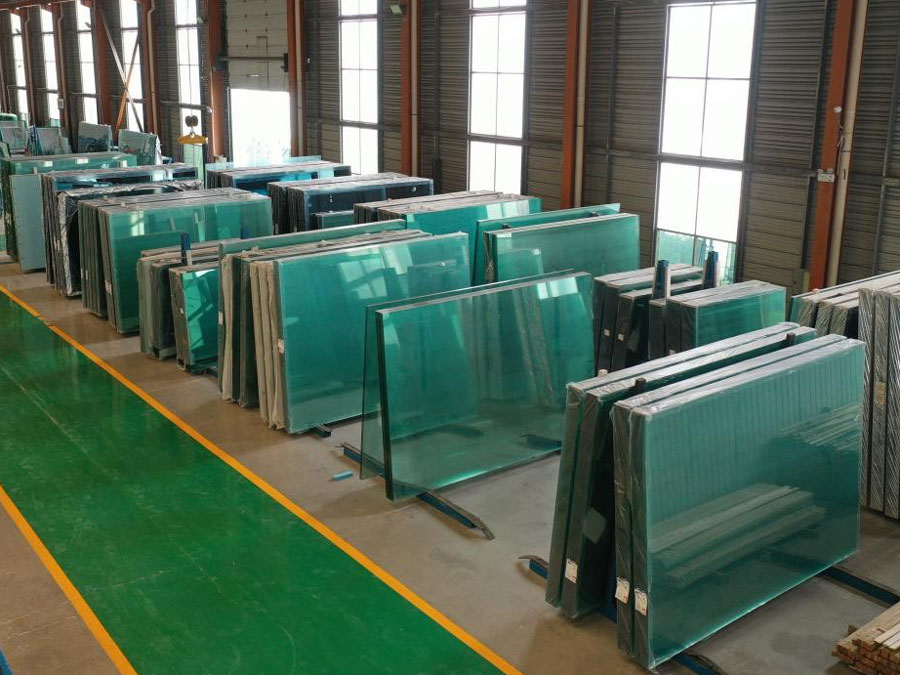西漢中期玻璃帶鉤
如果今天還有人把玻璃當(dāng)做寶貝,那么大家一定會(huì)覺(jué)得他是個(gè)怪人。但在古代,這個(gè)東西還真的曾經(jīng)很寶貝。我們讀古籍時(shí),常能看到類似“琉璃”“?琳”“藥玉”這樣的名字,其實(shí)指的都是玻璃。名字個(gè)個(gè)都是光閃閃的。《西游記》里寫沙和尚被貶下界,是因?yàn)榇蛩榱艘粋€(gè)“琉璃盞”,也就是個(gè)玻璃杯,就給貶到流沙河。今昔對(duì)比,真讓人一聲長(zhǎng)嘆。
廣州最早的玻璃發(fā)現(xiàn)于2200年前,來(lái)自西漢南越王趙濱的墓中。幾十年來(lái)陸陸續(xù)續(xù)出土的玻璃制品還有不少,特別是珠子多,高達(dá)萬(wàn)枚以上。這些珠子有本土產(chǎn),更多是外來(lái)貨,很多珠子和新疆發(fā)現(xiàn)的材質(zhì)一樣,可見(jiàn)是被同一張巨大的商貿(mào)網(wǎng)絡(luò)連接起來(lái)。這個(gè)網(wǎng)絡(luò),就是我們常說(shuō)的海上絲路、陸上絲路。當(dāng)我們站在博物館的展柜前靜靜看著它們,就會(huì)感覺(jué)到:原來(lái)這就是古往今來(lái)普通人的生活。
已知最早的平板玻璃出自南越王墓
考古學(xué)家們說(shuō),從上世紀(jì)五十年代初以來(lái),廣州地區(qū)發(fā)掘的兩漢墓葬超過(guò)千座。從西漢初期的南越國(guó)時(shí)期開始,各時(shí)期墓葬中發(fā)現(xiàn)大量玻璃制品。這類玻璃制品不見(jiàn)或少見(jiàn)于中原地區(qū),其中最典型的,莫過(guò)于以玻璃珠為主的串飾。數(shù)量很大,約有上萬(wàn)枚。
這些玻璃制品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中國(guó)傳統(tǒng)特色的仿玉玻璃,一類是富有外來(lái)特色的項(xiàng)鏈、手鏈、珠子等裝飾品,也就是古代所說(shuō)的珠璣、璧琉璃,此外還有一些玻璃器皿。
關(guān)于仿玉玻璃,南越國(guó)時(shí)期的主要器物是“璧”。西漢中期以后,璧的數(shù)量減少,代之以帶鉤等。其中,出自南越王墓的22件鑲在鎏金銅框里的平板玻璃,是迄今所知的時(shí)代最早的透明平板玻璃。
玻璃器皿主要是小碗,時(shí)代都是西漢中期,目前所見(jiàn)的三件都是深藍(lán)色半透明。
珠子是大宗。考古專家們說(shuō),珠飾最早是在南越國(guó)的高級(jí)貴族中流行,南越王墓中就出土了不少,根據(jù)位置推斷應(yīng)該是縫在衣物上作為裝飾的。國(guó)君都這么看重,可見(jiàn)其當(dāng)時(shí)的價(jià)值是相當(dāng)不菲的。
廣州出土的玻璃珠可以分為很多種類,來(lái)源相當(dāng)繁雜。根據(jù)多年來(lái)學(xué)術(shù)界的研究,目前已經(jīng)取得的基本共識(shí)是:中國(guó)古代玻璃屬于鉛鋇系統(tǒng),西方玻璃屬于鈉鈣系統(tǒng),還有一種鉀硅酸鹽玻璃。經(jīng)過(guò)分析可知,南越王墓出土的平板玻璃、玻璃璧和藍(lán)色玻璃珠含鉛鋇非常多,應(yīng)該是中國(guó)自制的。
不過(guò)這類主要流行于上層社會(huì)的仿玉玻璃數(shù)量畢竟不多。專家們指出,數(shù)量很大的玻璃珠從形式風(fēng)格和制作技術(shù)、材料來(lái)看,大多數(shù)有可能是從海上絲綢之路貿(mào)易得來(lái)。
三顆“蜻蜓眼”給我們講了一個(gè)埃及故事
廣州發(fā)現(xiàn)的玻璃珠里面,僅有三枚被稱為“蜻蜓眼”,都是南越國(guó)時(shí)期的遺物。這種小珠子,大有來(lái)歷。
專家研究認(rèn)為,蜻蜓眼玻璃珠是埃及的一大發(fā)明,最早的標(biāo)本為埃及公元前1400年~公元前1350年的玻璃珠項(xiàng)鏈。這項(xiàng)技術(shù)后來(lái)為腓尼基人和波斯人所掌握,地中海東岸和伊朗西部發(fā)現(xiàn)許多年代在公元前5世紀(jì)~公元前3世紀(jì)的蜻蜓眼玻璃珠。
西方風(fēng)格的蜻蜓眼玻璃珠最早在我國(guó)發(fā)現(xiàn)于新疆拜城的克孜爾墓地,年代大致相當(dāng)于西周至春秋戰(zhàn)國(guó)時(shí)期。在中國(guó)內(nèi)地出現(xiàn)大概是春秋末到戰(zhàn)國(guó)初期。它在西方有時(shí)是串成一大串項(xiàng)鏈,而在中國(guó)主要是作為單件來(lái)使用,或者和其他質(zhì)地的珠子合串。或許是因?yàn)檫\(yùn)至中國(guó)的數(shù)量稀少,格外珍稀。后來(lái)國(guó)內(nèi)對(duì)之也有仿制。但專家們認(rèn)為,無(wú)論哪種譜系的蜻蜓眼玻璃珠,其風(fēng)格都是源自西方,通過(guò)陸上和海上絲綢之路傳到中國(guó)。廣州發(fā)現(xiàn)的這幾枚,可能是西方珠子從海上絲綢之路傳來(lái)后,在廣州模仿其樣式制作的。
還有一類珠子被稱作“印度-太平洋珠”,也就是一種用拉制法制成,直徑一般小于5毫米,色彩呈不透明淡紅棕色及橙、黃、綠色等的單彩玻璃珠。根據(jù)國(guó)內(nèi)外學(xué)者的考證,這種玻璃珠首先可能是在印度阿里滿都生產(chǎn),它是當(dāng)時(shí)亞洲的一個(gè)玻璃制造中心,從3世紀(jì)到10世紀(jì),興盛了約7個(gè)世紀(jì)之久。這里的生產(chǎn)技術(shù)可能沿著海岸向東傳播,最終傳播到今天的嶺南地區(qū)。廣州發(fā)現(xiàn)的這類珠子,可能既有來(lái)自西方的產(chǎn)品,也有本地產(chǎn)品。進(jìn)口產(chǎn)品應(yīng)該通過(guò)海上貿(mào)易輸入,本土所產(chǎn)則是工匠的遷徙和原材料貿(mào)易帶來(lái)的技術(shù)傳播。

西漢中期珠飾
漢武帝時(shí),珍奇異寶就源源不斷輸入中國(guó)
實(shí)際上,對(duì)于玻璃所涉的“外貿(mào)”古人早有認(rèn)識(shí)。《三國(guó)志》里就寫:大秦,也即古羅馬帝國(guó),多產(chǎn)赤、白、黑、綠、黃、青等十種琉璃。唐李?也引《南州異物志》記載:“玻璃本質(zhì)是石,以自然灰治之。自然灰狀如黃灰,生南海濱”。從中我們可以得知,古人很清楚地知道玻璃是通過(guò)南海的海路輸入的。晉代煉丹家葛洪在《抱樸子》中記載:“外國(guó)作水晶碗,實(shí)是合五種灰以作之,今交廣多有得其法而鑄作之者”,也就是說(shuō)他不僅對(duì)玻璃的制作原理有所了解,也知道當(dāng)時(shí)的廣州一帶有不少掌握了相關(guān)技術(shù)的中國(guó)工匠。那么,那些最早輸入的玻璃珠具體是通過(guò)怎樣的一條或幾條線路,來(lái)到中國(guó)的呢?
自從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平定嶺南,設(shè)置桂林、南海、象郡算起,中國(guó)南方的海岸線和出海口就在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趙佗在嶺南地區(qū)建立南越國(guó)之后,嶺南與南海各國(guó)的海上交往又有更大的發(fā)展。通過(guò)今天大量的出土文物我們可以知道那時(shí)的海外貿(mào)易規(guī)模已經(jīng)相當(dāng)可觀,那么必然地,嶺南人民的海上探索開始當(dāng)遠(yuǎn)早于此。這種長(zhǎng)期的經(jīng)驗(yàn)積累,終于令番禺(即古廣州)在漢代早期發(fā)展成為中國(guó)九大都會(huì)之一。與其他都會(huì)相比,番禺的特色在于奇珍異寶比較多,是大宗商品交易集散地。東南亞、印度等地所產(chǎn)的明珠、璧琉璃、奇石等珍寶異物,從漢武帝時(shí)期就源源不斷輸入中國(guó);中國(guó)的絲綢等珍貴特產(chǎn),也通過(guò)這條線路不斷輸出到以上各地。
專家指出,通過(guò)玻璃珠這樣的小物件,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海上絲綢之路深刻地影響到了當(dāng)時(shí)人們的生活。它同時(shí)還展現(xiàn)了中國(guó)文化與南海諸國(guó)、中南半島、印度洋沿岸各民族、各地區(qū)的文化交流。在公元前三世紀(jì)到公元三世紀(jì),東西方國(guó)家之間的溝通,主要是經(jīng)過(guò)安息和印度地區(qū)。以今印度地區(qū)為中間站的海上中西交通,就是這樣一條由中西雙方共同開辟的海上商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