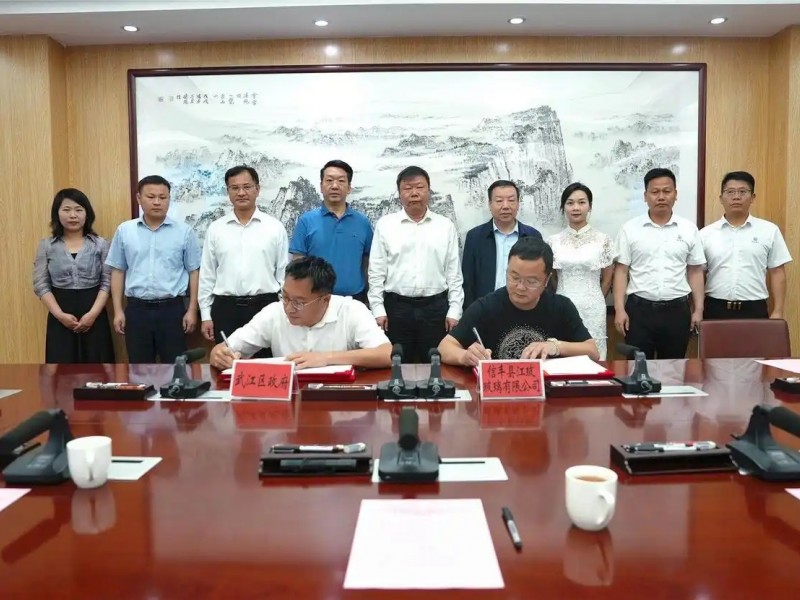談及玻璃,你會想到什么——是堅硬還是流動?是剔透純潔,還是清脆易碎?是日常生活中的瓶瓶罐罐,還是兒時擺弄手中的彈珠兒?2017年5月19日,一場關(guān)乎當(dāng)代藝術(shù)與玻璃的國內(nèi)外藝術(shù)家群展在798藝棧ICI LABAS畫廊開幕,策展人對它的回答是“危險與美麗”。

“危險與美麗——當(dāng)代藝術(shù)與玻璃展”為觀眾呈現(xiàn)了來自國內(nèi)7位優(yōu)秀藝術(shù)家以及來自包括美國、日本、韓國、捷克、波蘭、澳大利亞、斯洛伐克、荷蘭、拉脫維亞等國的14位知名國際藝術(shù)家的玻璃作品,同時展出的還有美國帕森斯藝術(shù)設(shè)計學(xué)院巴黎分院前院長,法國國立巴黎高等美術(shù)學(xué)院終身教授托尼 • 布朗(Tony Brown)的最新當(dāng)代藝術(shù)作品。

展覽開幕嘉賓及部分藝術(shù)家合影

托尼 • 布朗(Tony Brown)的作品與玻璃作品在當(dāng)代語境上對話
“玻璃是一種危險與美麗并存的材料,在對其本身的應(yīng)用和塑造上既有人為可控性,又有過程中的偶然與未知性。這不禁令人思考——藝術(shù)家在技術(shù)和材料面前究竟扮演一個怎樣的角色?是向往美麗的創(chuàng)造者,還是不懼危險的探索者?這正是‘危險與美麗’這一主題的指向。”本次展覽策展人汪付成在接受媒體專訪時如是解釋。

展覽現(xiàn)場
誠如策展人所言,玻璃似乎已經(jīng)成為我們每天都會觸及的材料,這樣一個經(jīng)常出現(xiàn)卻又最容易被忽視的媒介在藝術(shù)家的手中卻呈現(xiàn)出千姿百態(tài),展廳中的玻璃作品成為一種可以被感知、不再被忽略的存在,從一種單純的“材料”變成一件被賦予觀念的藝術(shù)品。在這一過程中,人們真正延展對于玻璃的思考,目睹它美麗的外形,卻同樣意識到它的脆弱與危險——藝術(shù)家在創(chuàng)作和工藝處理上,刻意凸顯或隱藏材料自身的特性,在危險與美麗之間轉(zhuǎn)換,以撩撥起觀眾內(nèi)心微妙的感受。
當(dāng)玻璃與當(dāng)代藝術(shù)家相遇,便碰撞出無限可能。本次展覽正是通過國際當(dāng)代藝術(shù)視野及平臺,以玻璃為呈現(xiàn)載體,重新發(fā)掘并賦予其當(dāng)代屬性,在更為廣闊的維度上,打破媒材與工藝的束縛和傳統(tǒng)思維定式,用當(dāng)代藝術(shù)與觀念澆筑新的玻璃語言,令這一傳統(tǒng)藝術(shù)形式重現(xiàn)生機(jī)。

羅賓·卡斯(Robin Cass)的作品
羅賓·卡斯(Robin Cass)的作品宛若來自深海的靈動生物。她是自然奇觀的搜尋者,更是探索生物可能的創(chuàng)造者。她直接用混合了描述性詞語的拉丁語給這些虛構(gòu)的“生物”命名,每一件作品都有著像明亮珍寶那樣的光感,即使是最簡單的構(gòu)造也顯得栩栩如生。它們裝裱在斑駁而獨具歷史感的船艙玻璃窗里,以一種新生生物的姿態(tài)呈現(xiàn),優(yōu)美而神秘。

大衛(wèi)·施納克作品《可穿透的花簇》

大衛(wèi) · 施納克作品《聚合磚塊》,將精美的玻璃酒杯融化壓縮
大衛(wèi)· 施納克(David Schnuckel)的作品圍繞“有意味的亂語計劃”展開,他首先制作出一組造型精美的玻璃酒杯,隨即將它們?nèi)诨嚎s并粘黏于一體。作品從“分裂”的興趣開始,引發(fā)出一個新觀念:如此多“復(fù)雜精致”的杯子集合成一個新的卻并不“復(fù)雜精致”的形態(tài)。試圖探索其過程中對于觀念的控制,偶然的要素,以及拒絕特定形式的思考。

趙顯成作品《雨中的米爾維爾》

作品細(xì)節(jié),宛若朦朧的隔世之境
《雨中的米爾維爾》是韓國藝術(shù)家趙顯成(Hyunsung Cho)的作品,其創(chuàng)作源自藝術(shù)家對城市生活故事與景物的迷戀,探討關(guān)于城市的視覺印象與個人記憶,試圖由此表達(dá)來自內(nèi)心情感和記憶深處的形象,呈現(xiàn)城市在日常生活中的豐富面貌。佇立在作品前,宛若隔著迷蒙細(xì)雨,望向心靈的遠(yuǎn)方,亦真亦幻,亦虛亦實,仿若夢中之境——那里我們曾經(jīng)抵達(dá),那里我們從未觸及......

彭怡作品《解構(gòu)系列》

彭怡作品《解構(gòu)系列》細(xì)節(jié)
彭怡的作品極具立體感,輕盈纖細(xì),錯落交織,融塑出時空的進(jìn)深,將美好與脆弱,東方與西方的不同氣息完美的呈現(xiàn)給觀眾。“中國是我的本土,而我卻在西方學(xué)習(xí)玻璃藝術(shù)。這種空間上的異置讓我重新觀望我們自有的文化內(nèi)涵,思考自我及社會身份。”藝術(shù)家彭怡在談及創(chuàng)作時說道,“因而,我從極具代表性的中國傳統(tǒng)鼻煙壺形象入手,對它的歷史發(fā)展進(jìn)行研究,并轉(zhuǎn)化成自己的語言,用燈工玻璃的形式進(jìn)行解構(gòu)。”一根根玻璃線段架構(gòu)起晶瑩剔透的解構(gòu)空間,或被拆解或被包圍的鼻煙壺仿佛一條通往歷史與記憶的線索和鑰匙,在當(dāng)代與傳統(tǒng),虛擬與現(xiàn)實,空間與時間中延展穿梭。

托尼 ·布朗作品《細(xì)胞》

托尼 · 布朗作品《真實與謊言》局部
除此之外,展覽現(xiàn)場同時展出了托尼 ? 布朗(Tony Brown)近兩年創(chuàng)作的作品。托尼 ? 布朗是以數(shù)字媒體裝置為創(chuàng)作媒介的當(dāng)代藝術(shù)家,近年來,他將自己的創(chuàng)作實踐拓展至繪畫、設(shè)計以及大型建筑項目領(lǐng)域,其作品試圖探討材料、技術(shù)與藝術(shù)家之間的創(chuàng)作關(guān)系。這批作品通過藝術(shù)家對機(jī)械的操控完成語言“轉(zhuǎn)述”,用技術(shù)在藝術(shù)家和繪畫之間架起一座橋梁,讓藝術(shù)家的主動創(chuàng)作和機(jī)械的被動執(zhí)行之間產(chǎn)生微妙的關(guān)系。這種對于材料、技術(shù)、可控性及未知的探索與玻璃藝術(shù)家們的思考不謀而合,當(dāng)代藝術(shù)作品與玻璃藝術(shù)并置展出,形成了不同媒材之間的交互對話。

克里斯塔·伊斯麗爾作品《副作用》
炎炎夏日,步入798藝棧ICI LABAS畫廊的空間與玻璃和當(dāng)代藝術(shù)相遇,足以令人身心沉醉清涼。剔透的不僅是玻璃材質(zhì)本身,更是對于美麗向往的心靈。而誠如本次展覽學(xué)術(shù)主持,中央美術(shù)學(xué)院張所家教授所言,希望人們看到作品時,并非停留于其材料或技藝層面,當(dāng)代藝術(shù)更多的是對于觀念的思考和情感的表述,本次展覽亦希望打破人們對玻璃的傳統(tǒng)看法,在當(dāng)代語境下構(gòu)建一種新的觀望方式。
據(jù)悉,本次展覽將持續(xù)至2017年7月30日。

朱麗越《天書》系列作品

展覽現(xiàn)場

李知勇作品《細(xì)胞結(jié)構(gòu)塊》

英格娜·奧德芮作品《老女人》

佐佐木雅浩作品《樹海》